为什么是“比例连带责任”? —中安科案简评
2021年5月1日,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确认其收到上海高院(2020)沪民终666号判决(下称“666号判决”)。该二审判决创造性地判处作为财务顾问的证券公司与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分别在25%和15%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这是我国已知的首例在证券虚假陈述案件中适用“比例连带责任”的案件,将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对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源流及其背后的法理精神进行梳理。
一、《证券法》第163条规定,中介机构的连带责任是刚性的
证券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责任是侵权责任,同时又受到《证券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制。关于中介机构的责任,2005年修订后的《证券法》第173条有明确规定:“证券服务机构……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与委托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在2005年的《证券法》修订之前,2003年的《证券法》则规定中介机构“对其所出具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并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修订之后的《证券法》删除“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的表述,并一直延续至今(最新的《证券法》相关规定见第163条)。因此实践中一般认为,2005年之后的《证券法》所规定的中介机构连带责任是刚性的,即连带责任与原责任在范围上是同一的,是全有或全无的关系。
二、《证券法》第163条与司法解释的冲突及原因
(一)《证券法》第163条实际上已被司法解释“修订”
2003年最高院出台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下称“《证券虚假陈述司法解释》”)第24条规定:“专业中介服务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违反证券法第一百六十一条和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虚假陈述,给投资人造成损失的,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但有证据证明无过错的,应予免责。”
上述规定事实上建立在2003年《证券法》的基础之上,2005年《证券法》修订之后这一解释与法律规定相悖,在法律解释上存在硬伤。有实务同仁认为,基于《证券虚假陈述司法解释》第24条的规定,“部分连带责任”的处理方式在我国《证券法》中存在适用空间,实无根据。同样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虚假陈述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复函》(2003年7月7日)亦在2005年《证券法》修法之前,无法绕开法律的明确规定而直接适用。
但在《证券虚假陈述司法解释》之后,最高院在多个其他的司法解释、文件当中重申中介机构的责任仅限于“其负有责任的部分”。
例如,2007年出台的《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区分会计师事务所的故意和过失,只有在故意的时候才与被审计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过失的情况下“应当根据其过失大小确定其赔偿责任”。又如,2020年7月15日发布生效的《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下称“《债券会议纪要》”)强调,对于中介结构“考量其是否尽到勤勉尽责义务,区分故意、过失等不同情况,分别确定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甚至,在2021年两会《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访谈中,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专委刘贵祥专门强调:“在有些财务造假案件中,中介机构对企业的财务造假活动,因为核查手段等限制没有发现,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也强调责任追究的过罚相当,责任与过错相一致,而不是采取一刀切,不问过错程度一律让中介机构承担全部连带责任”。
由此可见,关于中介结构责任的性质和范围,《证券法》第163条的规定与《证券虚假陈述司法解释》《债券会议纪要》等司法解释、司法文件的规定存在不同的理解。如果说从时间顺序来看,《证券法》的规定事实上已经被司法解释所“修订”,但是囿于《证券法》的法律位阶,实践中对于中介机构责任的认定,依然有非常大的争议。
(二)《证券法》第163条与司法解释冲突的根源
既然在连带责任的问题上《证券法》第163条的规定与司法解释存在明显冲突,这种冲突是怎么产生的?如上所述, “连带责任”首先是一个侵权法的概念,因此审视这一法律概念须放置于《民法典》的一般规则下。
从《民法典》关于侵权责任的类型可以看出,与连带责任相对应的是按份责任,并且两者都在多人侵权的语境下。对此,《民法典》第1168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第1172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两者的区分,事实上是基于“共同侵权”与“分别侵权”。从立法体例看,侵权人要么承担连带责任要么承担按份责任,并不存在所谓的在“同一损害”的范围内划分“部分连带责任”的解释空间。
与此同时,连带责任所解决的实际上是连带的侵权责任人与被侵权人之间的关系,连带责任人在承担责任后,内部之间可以相互追偿。对此,《民法典总则编》第178条规定:“二人以上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的,权利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连带责任人的责任份额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实际承担责任超过自己责任份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
具体到证券虚假陈述案件中介机构的,若如《证券法》第163条所规定的判令中介机构承担连带责任,中介机构可以主张其与发行人之间的内部责任分配。可能通常人会认为,这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在最终结果上中介机构理论上并不会承担更多的责任。
但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证券虚假陈述责任案件通常涉及众多公众投资者,损害赔偿金额巨大,通常的中介机构(尤其是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若承担如此巨额地赔偿责任,极有可能陷入破产的境地;另一方面,若作为“首恶”的发行人陷入到给付不能的困境中,中介机构被执行连带责任后事实上无法真的实现所谓的连带责任人之间的内部追偿;再者,连带责任人之间的内部追偿往往沦为扯皮,不利于尽快定分止争,中介机构亦实际上无法承担这种漫长的诉讼过程。
有可能是基于上述商业多人侵权责任的特殊性,美国证券法对于连带责任的适用是十分谨慎的。例如,1995年《证券私人诉讼改革法案》(PSLRA)即明确,除非被告是故意违反证券法律,否则应根据错误程度承担相当比例的按份赔偿责任。《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三次)》则强调“只有故意造成的不可分损害才能产生连带责任”。总体上来说,美国证券法是世界上多数国家借鉴的标杆,但我国2005年《证券法》修订时却“鬼使神差”地留下连带责任的法律解释问题。
三、666号判决的法理基础与深远影响
在666号判决之前,已发生的虚假陈述纠纷案件中,法院均判令中介机构对投资者的全部损失与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大智慧案”“金亚科技案”“昆明机床案”。666号案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对此,我们分析认为:
(一)“比例连带责任”具有实体法与法律理论的基础
除了《证券虚假陈述司法解释》《债券会议纪要》等司法解释、司法文件的规定之外,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从《证券法》第163条的规范中解释出“比例连带责任”的意涵?
我们认为,现行《证券法》第163条并未区分故意与过失,恰恰可以为“比例连带责任”与过失责任勾连提供解释的空间。换言之,在中介机构存在故意的情况下,判令其承担全部损失的连带责任,而在其过失的情况下根据过失的情况,判令其承担“比例连带责任”,应符合法律解释的原则。这一解释,实际上与《债券会议纪要》的规定是一致的。
再者,在中介机构仅仅存在过失的情况下,对“连带责任”的限缩解释应当援引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规则。台湾法判例认为:“他人所有物而为数人个别所侵害,若各加害人无意思上之联络,只能由加害人就其所加害之部分,分别负赔偿责任。”(王泽鉴:《侵权行为法》2016年版第427页)。事实上,在证券虚假陈述案件中,若非中介机构存在故意,其与上市公司或债券发行人之间,更接近于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关系。
(二)“比例连带责任”的待决问题与深远影响
“比例连带责任”虽然较好地呼应市场的声音,但是并非没有延伸出的问题。例如,中介机构在承担“比例连带责任”之后,是否有权向上市公司或债券发行人主张追偿?这一问题有可能存在截然不同的两种理解:
一方面,如上所述,所谓的连带责任其实解决的是多个侵权行为人与被侵权主体之间责任承担的问题,民法典总则编里关于侵权行为人之间的内部追偿权理论上还是应该适用的。但是另一方面,“比例连带责任”是建立在2003年证券法规定的语境中的,而2003年证券法规定的是中介机构“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责任,这里似乎暗含着一个前提,即法院已经对中介机构的责任部分做出分配。
总体上来说我们认为,666号案既落实《债券会议纪要》的精神,同样回应实践中广泛讨论的问题。事实上,在原有的证券虚假陈述案件中,囫囵吞枣式地判令中介机构就投资人地全部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并没有实际解决责任分担的问题。而666号案开历史之先河之后,中介机构在证券虚假陈述案件中到底应当承担多大程度上地责任,将可能出现“诸子百家”式的认定。这一方面是责任与过错相匹配的基本法律精神所须,另一方面对于法院如何使用其“自由裁量权”同样提出不小的挑战。
来源:百宸律师事务所


 0
0 0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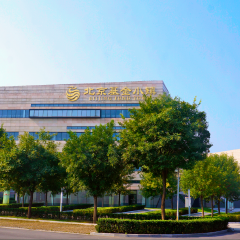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1102001195号
京公网安备:11011102001195号